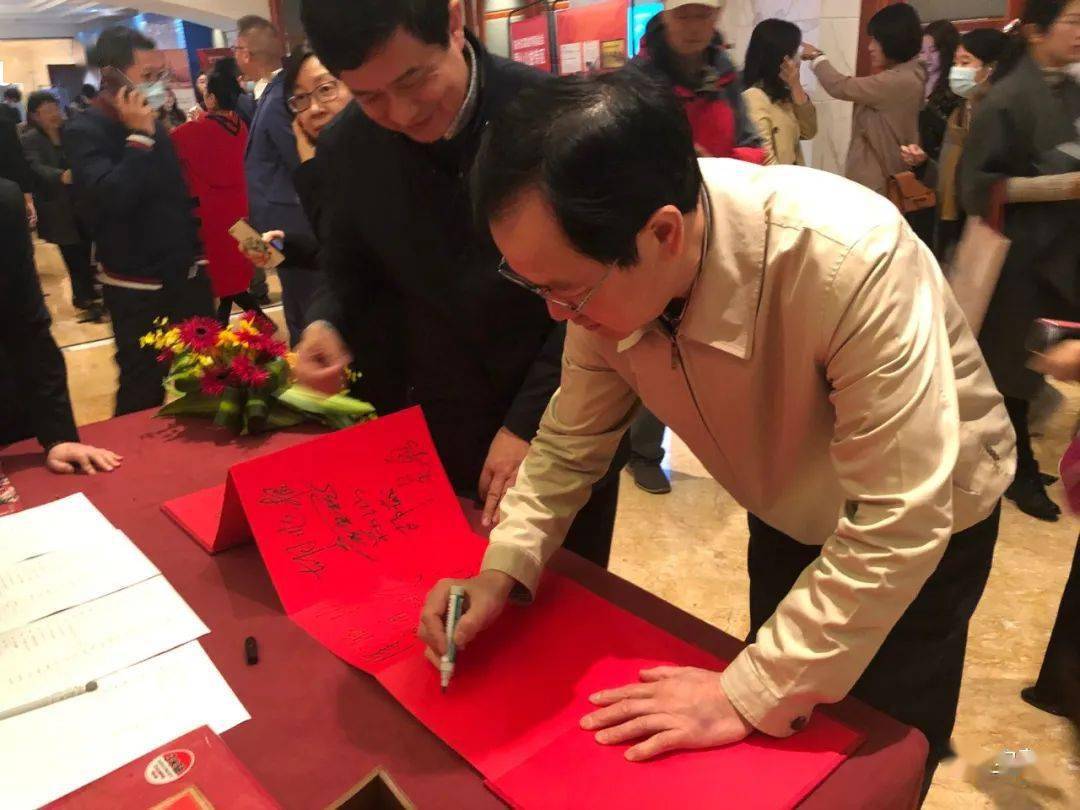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作家,同时也是独树一帜的书法家。已知鲁迅书赠中外友人和学生的字幅,据最新的《鲁迅手稿全集》(2021年9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、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)所录,有自作诗三十八题五十二幅,前人诗词和集句等二十二题二十七幅,均应视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书法作品中的瑰宝。
鲁迅后期在上海生活、写作将近十年,其间来往最多的日本友人,第一位无疑是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,第二位就是年青的日本学者增田涉。在为数可观的鲁迅书赠日本友人的字幅中,赠增田涉的两幅也特别引人注目。其中,1931年12月2日所作七绝《送增田涉君归国》,早已是脍炙人口的名作。而另一幅书于1935年3月22日的郑思肖作《锦钱余笑》第十九首,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,因为这幅珍贵书法的真迹最近在日本奇迹般地出现了。

增田涉
增田涉(1903-1977)原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生,师事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。1929年3月毕业后,协助佐藤翻译中国小说。两年之后,增田涉持佐藤的介绍信游学上海,经内山完造介绍,结识鲁迅。对此,他在《鲁迅的印象》(1948年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初版)一书的《绪言(略述认识鲁迅及受教经过)》中是这样回忆的:
(1931年)三月到了上海。最初只打算旅行一个月左右。当时对于中国文坛的事情,并没有特别注意,最初也不知道鲁迅在上海。只是因为得到佐藤春夫先生给内山完造先生的介绍信,一天去访问内山书店,恰好听说鲁迅正住在上海,而且每天都到内山书店来的。
我想,这是了不起的人,什么都得向他学习吧。在前面说过我对于他的尊敬,是由于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不过也知道作为作家,他是中国的第一人。因为曾读过上海版的《现代中国小说集》,又稍稍翻阅过上海发行的文学杂志《小说月报》。
最初会见他的印象,现在已经记不清楚。如果那时自己是暂时的旅行者,和鲁迅只会过一两回面,也许到现在还能够鲜明地记起当时的情况吧。但是后来一直经历了十个月,每天都和他接触,所以那第一个印象就自然地消失了。
总之,我怀着向他学习的心情,最初是计算着他出现的时间每天到内山书店去。大约是由于我问他学习中国文学,应该阅读什么书籍才好吧,他便给了我他所写的回忆幼年时代的《朝花夕拾》,我把它带回住所去读,不明白的字句或内容,第二天到内山书店去向他请教——这样继续了一段时间。……(增田涉著、钟敬文译:《鲁迅的印象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0年,第7页)
增田涉(1903-1977)
然而,增田涉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,是在1931年4月11日,该日鲁迅日记云:
晚治肴八种,邀增田涉君、内山君及其夫人晚餐。(本文所引鲁迅日记,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初版《鲁迅全集》第16卷,不另出注)
这比增田涉所回忆的该年3月见到鲁迅略晚,但鲁迅已经设家宴款待增田涉和内山夫妇,可见他们之间已谈得很融洽了。
从此以后,增田涉频频出现在鲁迅日记中。鲁迅到同文书院演讲《流氓与文学》,增田涉去旁听(4月17日);鲁迅专为增田涉购买《板桥道情墨迹》和信笺(4月19日);还带增田涉至郑振铎寓一并欣赏“明清版插画”(6月19日)。他们经常互访、互赠礼物,并一起观看电影、歌舞和画展,包括“一八艺社展览会”(6月12日)。增田涉比鲁迅小二十二岁,两人之间的“师弟”情谊可谓与日俱增,令人感动。
当然,鲁迅和增田涉之间更为重大的事情,是鲁迅向增田涉讲解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帮助增田涉翻译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对此,增田涉也有很具体的回忆:
跟着开始了对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学习,这是本来就打算翻译的(内山完造先生也劝过我),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听他讲解的。那时候,已经不是在内山书店的店头,而是直接去鲁迅的住宅了。在内山的“漫谈”(当时这样说)一结束,就和他一道去他的住宅(从内山书店到他家约二、三分钟的距离)。然后,两人并坐在书桌边,我把小说史的原文逐字译成日文念出来,念不好的地方他给以指教,关于字句、内容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彻底地询问,他的答复、在字句方面的解释,是简单的,在内容方面,就要加以种种说明,所以相当花费时间,大约从午后的两点或三点开始,继续到傍晚的五时或六时。当然也有时转入杂谈,或参加他对每天发生的时事的意见或批评,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消费在那本书的讲读上。(增田涉著、钟敬文译:《鲁迅的印象》,第8页)
当时,鲁迅住在北四川路194号拉摩斯公寓(今北川公寓)A三楼四号,离内山书店确实很近很近。增田涉回忆的“漫谈”,系当时内山书店经常举行的中日文化人的“漫谈会”,如鲁迅日记1930年8月6日就记云:“晚内山书店漫谈会,在功德林照相并晚餐,共十八人。”可见增田涉也曾是“漫谈会”的参加者之一。
增田涉的回忆是很感人的,鲁迅为向增田涉讲解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。鲁迅日记中并未记录对增田涉开讲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始于何时,但有结束的明确记载,时在1931年7月17日:
晴,下午为增田涉讲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毕。
此后,鲁迅还为增田涉讲解了《呐喊》《彷徨》等,当然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讲解得最为详细。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,增田涉在日本学界崭露头角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日译本,其实是鲁迅与其合作的结晶,保存下来的《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》(1988年日本汲古书院初版,中译本1989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)也是一个生动的证明。
1931年12月初,增田涉满载与鲁迅的深厚师生情回国。鲁迅12月2日日记云:
作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一首并写讫,诗云:“扶桑正是秋光好,枫叶如丹照嫩寒。却折垂杨送归客,心随东棹忆华年。”
增田涉回国后,一直与鲁迅鱼雁不断,还曾专诚来沪探望鲁迅。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日译本也终于在1935年由东京赛棱社初版。鲁迅于1935年6月9日为日译本写了序,其中回忆道:
回忆起来,大约四五年前罢,增田涉君几乎每天到寓斋来商量这一本书,有时也纵谈当时文坛的情形,很为愉快。(鲁迅:《〈中国小说史略〉日本译本序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年,359页)
这正可与增田涉在《鲁迅的印象》中的回忆相映证。
接下来就应该说到鲁迅书赠增田涉《锦钱余笑》诗了。正因两人的“师生”情谊很深厚,1935年1月18日,增田涉致信鲁迅,在信中提出一个请求,希望鲁迅为其表舅今村铁研(1859-1939)写一幅字。今村铁研是日本岛根县人,当时在乡村行医,他久闻鲁迅大名,很想得到鲁迅的一幅字。鲁迅在1月25日回信增田涉:
写字事,倘不嫌拙劣,并不费事;请将那位八十岁老先生的雅号及纸张大小(宽,长;横写还是直写)见告,自当写奉。(本文所引鲁迅致增田涉信译文,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初版《鲁迅全集》第14卷“致外国友人部分”,不另出注)
显然,鲁迅乐意为增田涉表舅写幅字,而且十分周到,如何称呼、写多大字幅、横写还是直写,都要问个清楚。其实,鲁迅为他人写字,大致有三种情形:一是主动写赠亲友,如书赠许广平数幅和《送增田涉君归国》等即是;二是友朋索字,如1932年12月31日一天里就为郁达夫和日本友人书写了五幅字,这是鲁迅所写字幅中的大宗;三是友朋为他人求字,如郁达夫就曾数次请鲁迅为其友人写字。增田涉为表舅求字也属于第三类,鲁迅同样认真对待。
但是,因为事忙,鲁迅没有及时挥毫。想必是增田涉又来信催问,鲁迅在1935年2月27日致增田涉的回信中说:
手书两封先后拜读。近来为编选别人的小说,忙极。给铁研翁的字,还未写,以后寄到东京去罢。……
“雅仙纸”其名未曾听过,也许是为向日本出售而特制的东西(名称)罢。中国有“画心纸”或“宣纸”(因在宣化府制造的)。《北平笺谱》用的就是这种纸,此次仍将用这种纸。
鲁迅在此信中不但解释了为何字幅未能及时写,也许增田涉在信中询问字幅将用何种纸写,鲁迅又作了详细的解答。一年之前,鲁迅已赠送增田涉一部《北平笺谱》。这也是鲁迅为他人写字,与之讨论最多的一次。
此信发出后不到一个月,鲁迅的字终于写好了。在3月23日的信中,鲁迅通知增田涉:
今天已将我写的字两件托内山老板寄上,铁研翁的一幅,因先写,反而拙劣。
增田涉想必及时收到了内山寄去的字幅,满心喜欢了。有趣的是,这件事并未到此结束,这有鲁迅1935年4月30日致增田涉的信为证:
我的字居然值价五元,真太滑稽。其实我对那字的持有者,花了一笔裱装费,也不胜抱歉。但已经拿到铁研先生的了,就算告一段落,并且作为永久借用了事。
原来今村铁研得到鲁迅的墨宝后,十分满意,尽管鲁迅自认“拙劣”。今村不但及时将其裱装,还托增田涉转奉润笔,这大概是鲁迅写字得到的唯一一次润笔,以至鲁迅在信中如此作答,鲁迅的幽默风趣由此可见一斑。
更重要的是,鲁迅托内山寄给增田涉的字是“两件”,一件为今村铁研所书,另一件就是为增田涉所书了。这在鲁迅1935年3月22日的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:
晴,午后昙。……为今村铁研、增田涉、冯剑丞作字各一幅,徐訏两幅,皆录《锦钱余笑》。
也就是说,由于今村求字,鲁迅也为增田涉大笔一挥,写了一幅《锦钱余笑》。对增田涉而言,这真是意外之喜。而对鲁迅而言,则是再次对这位“增田同学仁兄”表示了自己的关爱之情。鲁迅为增田涉所书的郑思肖《锦钱余笑》第十九首照录如下:
生来好苦吟,与天争意气。自谓李杜生,当趋下风避。而今吾老矣,无力收鼻涕。非惟不成文,抑且错写字。
所南翁锦钱余笑之一录应增田同学仁兄雅属鲁迅

鲁迅为增田涉所书的郑思肖《锦钱余笑》第十九首
这件鲁迅长条直幅,字心一百乘以三十厘米,日式裱装,裱装全幅两百零五乘以四十厘米,完好无损,在现存鲁迅字幅中是极为少见的大幅,足可用珍若拱璧来形容。
增田涉在《鲁迅的印象》之《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及救人精神》这一章中也专门谈到了鲁迅这幅字:
鲁迅逝世前一年,我的一位老年亲戚,托付我请他写字,顺便我也请他写一幅,给我的是写在条幅上的郑所南的《锦钱余笑》中的一首:(下略——笔者注)
这虽然不是他自己做的,也可以认为是在这儿寄托着他当时心境的一部分吧?幽默里多少有些辛酸的心情。也许是由于身体的老病吧,感觉到他那无力收鼻涕的心境的一部分。我看了忽然联想到芥川龙之介的俳句:鼻水呀,总是挂在鼻尖上。(大意)彼此在构想上有着类似的东西,意境也相通。两人看来都有着有劲的鼻梁,但自己意识到鼻梁上时有鼻水的点滴,因而出现了自嘲的心理阴影。——我以为这是人的一个方面。(增田涉著、钟敬文译:《鲁迅的印象》,96-97页)
显而易见,增田涉不但回顾了鲁迅书赠郑思肖诗幅的经过,而且对鲁迅为何选择书写《锦钱余笑》第十九首也作了出自他自己所理解的解读,把鲁迅与芥川龙之介作了很有意思的比较,还透露鲁迅晚年仍念念不忘翻译芥川龙之介,很值得留意。
确实,鲁迅在1935年3月22日这一天,一口气接连书写了四首不同的郑思肖《锦钱余笑》中诗赠人,这在鲁迅的书法史上绝无仅有。除了给今村铁研和增田涉写的两幅,还给许广平姑妈之子冯剑丞写了一幅,给《人间世》、作家徐訏也写了一幅。3月21日鲁迅正好收到徐訏一信,很可能是求字,第二天就一并写了。不过,鲁迅3月22日日记有一个小误,日记记“徐訏二幅,皆录《锦钱余笑》”,一幅直幅确是《锦钱余笑》第二十首,另一横幅却是李贺《绿章封事》诗之一联,而非取自《锦钱余笑》。
郑思肖(1241-1318),字忆翁,号所南,南宋遗民,诗文均自成一家,尤以《心史》著名于世。《锦钱余笑》组诗二十四首(《锦钱余笑》二十四首,参见陈福康校点:《郑思肖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年,232-235页)当为思肖晚年之作,大都为抒发胸中块垒,也颇有打油自嘲的意味,在明清诗中别具一格。鲁迅为比他年长的今村铁研写字,选择《锦钱余笑》中诗,固然较为合适,一口气为增田涉、冯剑丞和徐訏也都写了《锦钱余笑》中诗,更表明他对郑思肖其人其诗的欣赏。有论者认为,鲁迅这次挥毫,“大约也有一点借以发泄自家胸中块垒的意思。1935年顷,上海左翼文坛问题多多,鲁迅的情绪颇为郁闷。”(顾农:《鲁迅手书之古人诗词》,《诗人鲁迅:鲁迅诗全考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20年,414页)窃以为这个看法也很值得注意,从这幅字中或可窥见鲁迅晚年心态之一端。
鲁迅为增田涉所书的《锦钱余笑》第十九首字幅,在鲁迅后期的书法作品中占着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。此幅不仅带有些鲁迅自嘲的意味,不仅是鲁迅与增田涉“师生”情谊的又一次生动体现,其书法艺术本身的价值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郭沫若论鲁迅书法云:
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,所遗手迹,自成风格。融冶篆隶于一炉,听任心腕之交应,朴质而不拘挛,洒脱而有法度。远逾宋唐,直攀魏晋。世人宝之,非因人而贵也。(郭沫若:《序》,《鲁迅诗稿》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1991年,序文第2-3页)
这段话是评判鲁迅书法的不刊之论。“融冶篆隶于一炉,听任心腕之交应”,在鲁迅书赠增田涉的这幅字中,也得到了充分而有力的展示。这幅字融冶篆隶,笔墨圆润,又一气呵成,理应视为鲁迅大幅书法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。
增田涉逝世后,他的日、中、英文藏书全部捐赠其最后任教的日本关西大学,其中包括《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》手稿并鲁迅题赠的五种著译。我1997年秋在日本访学时,曾至关西大学“增田涉文库”查阅,又发现了还未著录的鲁迅亲笔题赠增田涉的《引玉集》,并为此撰写了《“增田涉文库”鲁迅题词发现记》。现存鲁迅写给增田涉的五十八通信札和鲁迅书赠增田涉的《送增田涉君归国》诗真迹,也均已珍藏于增田涉出生地日本鹿岛历史民俗资料馆。唯独这幅《锦钱余笑》第十九首诗幅原件,一直不露真容。
有必要说明的是,鲁迅所书《锦钱余笑》第十九首诗幅不甚清晰的照片,最初出现于1976年文物出版社初版《鲁迅诗稿》,而最新的《鲁迅手稿全集》所收录的则是依据1998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版《鲁迅诗稿》再影印,仍非依据原件。至于鲁迅手书的另三件《锦钱余笑》诗幅,赠今村铁研的第二十二首,《鲁迅手稿全集》也据1998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版《鲁迅诗稿》再影印,赠徐訏的第二十首原件已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,而赠冯剑丞这幅至今未见,恐已不存矣。因此,这次赠增田涉的这幅《锦钱余笑》第十九首真迹重现世间,实在是近年来鲁迅手迹发现的大事,不能不令我倍感振奋,也应该引起鲁迅研究者和鲁迅书法研究者的关注。
与鲁迅赠增田涉诗幅同时出现的,还有增田涉自己的一幅汉字字幅,上书“鸟寂云闲 竹疎风细黄幻人书”。增田涉有书斋名“黄幻堂”。这幅字虽不知写于何时,但增田涉的书法极为少见,也是很难得的。

增田涉自己书写的汉字字幅